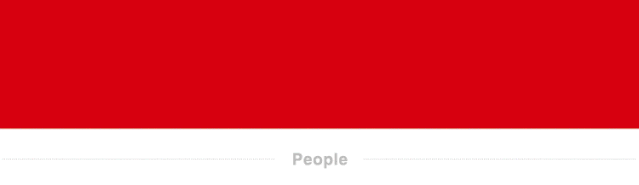

年过八旬的德国艺术家乔治·巴塞利兹 (Georg Baselitz) 作为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曾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为德国艺术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自1960年以来亦对国际艺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今,他仍为自身的艺术创作是否在挑战观众而感到激动和快乐。艺术家迄今为止最大型的回顾展“Baselitz: A Retrospective”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正在进行中,汇集了其创作生涯中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油画和雕塑作品。而他的个展“Hotel garni" 也随着Thaddaeus Ropac 画廊在首尔设立新空间拉开帷幕,呈现了其新近创作的十二幅油画和十二幅手稿,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颠倒反转形象,也开拓了新的绘画手法。
这位难以被归类的艺术家,在长达六十年的艺术生涯里不断革新自身艺术实践,从不落入任何风格的窠臼。他运用油画、雕塑、版画、手稿等不同媒介进行创作,并不断定义着媒介的包容度。艺术家甚至曾声称要画出尚未存在的图像,去唤醒过去被拒绝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被破坏的秩序中,一个废墟的风景中,一个人在废墟中,一个社会在废墟中。我并不想引入一个新的秩序。我已经看够了所谓的秩序。我被迫对一切提出质疑。我不得不重新‘天真’起来,重新开始。我既没有意大利风格派的敏感度,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教育或哲学训练。但我是一个风格主义画家,因为我使事物变形。"
——乔治·巴塞利兹
巴塞利兹,原名为汉斯-乔治·科恩(Hans-Georg Kern),1938年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巴塞利兹小镇,最初于原东柏林的汉堡造型艺术学院(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Künste Hamburg)就读,后因“社会政治欠缺成熟”而被开除学籍。当时他便已经意识到,艺术的唯一社会有效性在于其激烈的无畏性以及对道德和政治指令的不可约束性。1963年在西柏林完成学业期间,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出生地名“巴塞利兹”。也是在那一时期,恰逢“国际艺术与抽象主义”的盛行,巴塞利兹坚决反对抽象绘画的统治地位,常在自己的具象作品中融入令人叹为观止的意象,旨在引出观者的强烈体验。例如,1958年由美国中情局赞助的“美国前卫艺术展”[Die neue amerikanische Malerei (The New American Painting)]在柏林的展出,让他在震撼之余意识到这些战后创作的抽象艺术潮流中所普遍存在的历史失忆[尽管后来,巴塞利兹承认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是美国最好的欧洲画家]。他以一种讽刺的方式重申自己的日耳曼(萨克森)文化根源,也找到了当时个人创作的出口,这有赖于19世纪的德累斯顿画家路易-费迪兰德·万·雷斯基 (Louis Ferdinand von Rayski,1806-1890)的作品启发,后者有意在诠释权力富贵的萨克森贵族肖像画中凸显不甚完美的酗酒细节。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巴塞利兹通过情景想象和游历战后衰败国家的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不朽人物的绘画,即“英雄”(Helden)系列,并开始以碎片化的形式创作“断裂”(Frakturbilder)系列,试图对绘画传统进行解构。1969年,他发现对于摄影照片的日渐依赖也强化了绘画中的图示性,同时对于模特重复出现(如自己的妻子埃尔珂和身边亲近的朋友)的情况也令艺术家开始反思。为了颠覆这种被他认为是趋向“和谐”的画面,巴塞利兹首次以颠倒翻转的构图作画,这种新颖的方式彻底改变被视为走向穷途末路的传统绘画,并被沿用至今,成为其作品的典型特征。二十世纪70年代,巴塞利兹开始用手指直接作画(Fingermalerei),这使得他对色彩和材料的运用更为自由流畅,于其80年代的表现主义作品中尤为突显。
“我一直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阻碍了我的绘画创作?事实上,一直阻碍我的——即便现在已有显著改善——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自我的意识禁锢了我,甚至在创作中也无法避免。从艺六十年来,我一直试图从自身剥离出来。如今我终于可以宣告,最近二十年来我做到了,最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乔治·巴塞利兹

乔治·巴塞利兹,《Modell für eine Skulptur (1979-1980)》

“Baselitz: A Retrospective”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二十世纪80年代在巴塞利兹的艺术生涯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80年,他与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一起代表德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标志着他首次涉足雕塑领域。《Modell für eine Skulptur (1979-1980)》就是一件用电锯切割并上色的木质雕塑,不但其冰冷,机械和残酷的工具与其绘画方式如出一辙,人物半坐并做出仿佛纳粹手势的姿态更是备受争议。在蓬皮杜的此次回顾展中也囊括了艺术家的若干件雕塑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将他多年来在绘画中坚守的创作原则延展到了立体的层面上。
往后十年里,他参加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展览,逐渐在艺术界建立声誉,包括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的“绘画的新精神”(A New Spirit in Painting,1981年),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举办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982年),以及在美国巡回展出的“表现:德国新艺术”(Expressions: New Art from Germany,1983年)。1995年,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为巴塞利兹举办了他在美国的首个回顾展。


Q = 贺潇
A = 巴塞利兹


Q:您将此次在Thaddaeus Ropac 画廊首尔空间举办的个展命名为“Hotel garni”(通常指价格便宜的城市酒店)。这个展览题目会让人想起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的名画《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在描绘了巴萨罗那红灯区的年轻女性的同时, 画作汲取了来自非洲和大洋洲艺术中的视觉线索。那么,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与这件毕加索的杰作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展览标题是否暗示了您的绘画观?
A: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一直有意识地关注着很多艺术家的晚期作品,特别是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我会问自己,这些晚期作品的质量相对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差,或者并没有改变。就毕加索来说,他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质量急剧下降。他去世后,作品也出现了市场价格暴跌。但与此同时,评论界对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如今,毕加索晚期画作的市场估价还是很高。我许多作品的标题都提到了这种现象。“Hotel garni”也是。酒店有很多种类型,最便宜的是按小时计费,在那里你不需要过夜,而是呆上几个小时。


左:乔治·巴塞利兹, 《请勿打扰》, 2021年
右:乔治·巴塞利兹, 《无题》,2021年
Q: “Hotel garni” 中的一些作品,如《请勿打扰》(Do Not Disturb)和《单人房、单人床》(Einzelzimmer, Einzelbett)呈现倒置在椅子上的单人或双人形象;展览中其他作品则让人想起您的《抵达》(Ankunft,2018),它参考了杜尚(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No.2)。您为什么会一直回收和重新使用这些以前的题材,而不是开启新的主题?
A:自从1969年以来,我就一直使用相同的图像。因为,我主要关注的是转化“方法”,即形式方法。当然,这样做会产生一种连续性,也就是重复性。
Q:“Hotel garni” 中的布面作品采用了接触式印相的绘画方法,使作品最终在黑色画布上呈现绘画痕迹。虽然您以前也在黑色画布上描绘,但是什么让您在职业生涯中的这个时刻发展出这种技法?
A:首先,这是我头脑里的一个过程。我是说,一个追求变化和新方法的过程。这很重要。但也得说,身体的局限性导致了新方法的出现。我身体已经不如以前健康了。

Q:与您过去的作品相比——例如在《抵达》中,您直接在黑色画布上作画,然后再添上“雾”的效果——您现在采用的接触式印相方法,是否让您创造出更抽象的画面?特别是,这些绘画中的光影效果堪比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中的“墨渍图”,它们受到过精神分析理论的驱动吗?
A: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这些作品不是治疗性的。而只是一个在寻求创新的同时,不偏离自己的轨迹的过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你只能对做过的事进行比较,没做出来的事是无法用来作比较的。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人们只有在它出现在画布上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乔治·巴塞利兹, 《无题》,2021年


左:乔治·巴塞利兹, 《无题》,2021年
右:乔治·巴塞利兹, 《Hotel garni》,2021年
Q:您本次展出的纸上作品使用了红色和黑色墨水,这令人想到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有用红色和黑色粉笔作画的艺术家。意大利语中的“Disegno”一词(文艺复兴艺术理论中的概念之一,意指用线及轮廓来表现物象的方法)被翻译成德语为“Dasein”(“此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之意指“存在”或“存在在那里”。纸张是您将当下的状态视觉化呈现的主要媒介吗?您是如何将纸上作品转化为布面作品的?
A:请放过海德格尔和其他所有这些哲学家吧。总之不要把“存在”扯进来。我的作品里有思考也有实践。对我来说,这是如何将思想付诸实施的问题。我所思考到的东西有一部分被呈现在画布上或纸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靠误打误撞了。
Q:展览的新闻稿中提到:“今天,图像要比飞机还快,这可真令人兴奋。” 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十年中,您的创作一直建立在照片的基础上,那么数码图像的加速——无论是成像还是流通——是否影响了您在绘画实践中使用它们的方式?
A:没有,只是我们提供信息的方式改变了。基于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我们可获取的信息要比二十年前多得多,但这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么多的绘画艺术家。当然,亚洲艺术家也包含在内。



“Baselitz: A Retrospective”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Q:近期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回顾展,显然不是您的第一次回顾展。您对这次展览的呈现是否满意?它与近些年其他的回顾展,如2018年在贝耶勒基金会博物馆(Fondation Beyeler)举办的回顾展或赫希洪博物馆和雕塑园(The 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的“六十年”(Six Decades)相比,有何不同之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您有什么新的发现(或再发现)吗?在您的实践中,什么是始终如一的?对于如此规模的展览,总会有一些作品很遗憾地被排除在外,是这样吗?
A:首先得说,回顾展有始有终,它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走出展览,只要展览内容结束了,就暂时没有什么了。人们可以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无法改变的是这之前的一切,至多是可以对作品进行整理和筛选。和所有博物馆一样,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空间有限,因此观众只能看到一部分精选作品。我认可这些选择。但有些东西是未能展示的,比如其他应该出现在那里的艺术家。对我来说,这种回顾展是一种体验:我在多大程度上依旧是创造出你眼前所见之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现在我只是个旁观者?在我看来,我其实已经在出口处了。从展览构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在此期间我不但画了新作品,而且现在我又在构思新作了。
Q:您曾经表示,2018年贝耶勒回顾展中的最后一个展厅是令人不安的。在这次回顾展中,什么可能会对观众有一些挑战?
A:在贝耶勒基金会的展览中,最后一个展厅几乎完全展示此前从未展出过的新作品,这很让人不安。而在蓬皮杜的展览中,最后一个展厅展出了约十年以来的作品,它们其实已经构成一种回顾,因此不会像贝耶勒的展览那样带来不确定性。


Q:您从1960年代开始使用分散性乳液作画,这是一种比油彩更平坦、更便于叙事的材料。这个转变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您绘画中的倒置人物为何也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
A: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的作品主要以油画为主。我很少会使用其他材料。材料从来不会抑制我在方法上做出改变。说到底,我从来没有因为绘画材料而停止实验。
Q: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中情局赞助了一场展览,有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弗兰兹·克莱恩(Franz Kline)等人参加,这场展览对当时作为一位年轻艺术家的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并未追随国际当代艺术的潮流,如1960年代末美国波普艺术和极简主义,70年代在德国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掀起的热潮。然而,您显然很熟悉他们的作品。您为何对这些艺术界潮流不为所动,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您会选择不同的方向吗?
A:正如你所看到的,我选择的方向与我遭遇的情境完全相反。我是说——而且我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出客观的作品。你说的那些东西也都是艺术家独特而主观的表达,即便是它们被冠以某个团体的名字,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你也可以说,时代的列车已经满员,没有我的位置了。顺带说一句,波洛克在1958年就去世了,我们在此讨论的抽象派已经被波普艺术所取代。

乔治·巴塞利兹, In der Tasse gelesen, das heitere Gelb, 2010年
Q:您从60年代末开始用照片作画;但您并不贪恋图像。您是如何决定要选用哪张照片或图像的?为什么有一些图像在您作品中反复出现,例如坐立的夫妇(可能是您和您妻子埃尔珂ELKE)?您在创作双人画(您的妻子和您)时,是否掺杂了个人的感情成分(这毕竟是您认识最久的两个人)?
A:我作品中使用的照片捕捉了记忆。这些照片并非被转化为图像,而是存储了记忆。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会使用相同的老照片。为什么要改变呢?
Q:您为什么会认为您的作品是表现主义,而不是新表现主义?
A:在德国,我们发明了表现主义。这是一个仅限于1920年代的图像世界,与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并驾齐驱。它总是被描述为德国表现主义。这件事一开始让我很不舒服。但后来我也习惯了被称为德国艺术家。放眼当下的艺术界,这依旧是让艺术家“国际化”的最好机会。
Q:您的全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战后德国的意识形态,这在某些方面与政治正确倾向的加剧形成呼应。是什么让您决定在您的实践中保持一个独立于意识形态的位置?
A:我发现我不喜欢意识形态,它们会打扰到我,让我的头脑变得混乱。我讨厌政治正确。我讨厌盲从因袭。我认为,即便是民主也可能阻碍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想远离所有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措施。否则,我就不得不对南北韩发表一番言论,前提是经过了有意义的思考。最后你会发现,只有当你发现什么是政治不正确时——即你得给自己确立一个对手——你才能找到政治正确。我们真想这样生活吗?
Q:您作为一个在过去六十年中一直持续创作的八旬老人,是什么激励着您去工作室的?是什么让您继续创作这些挑战观众内心的绘画?
A:只要能挑战到观众,我就会很高兴。如果不工作,我会不快乐。
Q:您的艺术实践以绘画和雕塑为主,您对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有什么建议吗?
A:他们应当停止绘画!这样我能过得更好。
采访、撰文/贺潇
*若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由蓬皮杜艺术中心与Thaddaeus Ropac画廊提供
Baselitz: A Retrospective
蓬皮杜艺术中心
2021年10月21日-2022年3月7日
